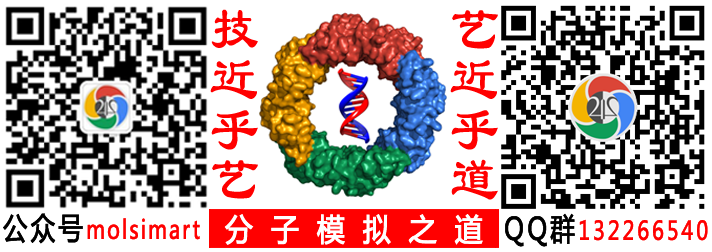结语
变异的电脑
2013年,一部智能手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相比,价格要便宜100万倍,体积小10万倍,运算能力大几千倍。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以同样数量的钱能够买到的计算能力增长了10亿倍。以100美元的代价存储的数据量的增长倍数更是天文数字。一个人在2012年可以以100美元购买1 TB的存储设备,相比之下,在1961年购买28 M的存储设备要花115 500美元(IBM 1301计算机I型)。人们能打印或电子邮寄的文件数也增长了好几个数量级。文件传输速度从数天缩短到数毫秒,提升达9个数量级。电脑使用者可用的免费信息从20世纪60年代的办公室文件迅猛增长到2013年的300亿个网页。
本来,计算技术就是速度。一台电脑就是一部机器,能在几分之一秒内完成许多人需要干很多天的计算量。50年后,这一简单的概念已经导致了对计算能力完全不同的解读。现在计算能力意味着两件事:接触到海量的知识,以及无处不在的通信。前者已经建立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人们可以向浩瀚如烟的动态知识库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乌托邦。后者则产生了虚拟社区。这两种效果与电脑的计算速度,也就是计算机原本的目的有何关系,已经不再显而易见了。
计算机把人类社会转变成一个数字社会,人类成为数字数据的创造者、保管者、传递者和浏览者,这些数据把世间万物编码成为布尔代数。这种对世界进行编码的方法远比过去基于纸面的社会来得有效。与此同时,电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信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把一个简单的电话变成了包罗万象的个人数字助理,而语音通信只是它用途的沧海一粟。
硅谷长于开发,而非研究
硅谷被广泛地认为是这场革命的标志。然而,计算机并非硅谷的发明,硅谷从来没有世界上最大的硬件公司或软件公司。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硅谷也没有发明电话、手机和智能手机。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在使这些产品得以迅速传播,并将一个产品臻于完美的为世界所用这一方面,硅谷功不可没。
硅谷的创业公司擅长发掘那些源自美国东海岸和欧洲的大型研发中心、后来来到了旧金山湾区,但是未被充分利用的发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家东海岸的公司,它发明了半导体电子,肖克利把它带到了山景城。IBM也是一家东海岸公司,在其圣何塞的实验室发明了数据存储技术。施乐也是东海岸的公司,在其帕洛阿图研究中心完善了人机界面。美国政府发明了互联网,它选择斯坦福研究所作为其节点之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明了万维网,而第一个美国的万维网服务器设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如此等等。
实际上硅谷最大的研究中心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中心,而是“研发”中心。它们更偏重于“开发”而不是“研究”。它们与AT&T的贝尔实验室或者IBM的瓦特森实验室(Watson Lab)无法相提并论,这两个实验室都曾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有人会争辩说,硅谷的研究工作是在斯坦福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但是这两个研究中心也没有在技术方面产生过可与晶体管或万维网相比的里程碑式的发明。它们更擅长孵化创业企业,而不是为这些创业公司发明技术。
不要盯着硅谷去猜测下一个高科技重大发明是什么,它将出现在别的地方。硅谷会挑选那些将对普通人和上班族的生活产生革命性改变的发明予以发掘。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产生过很高级的技术,比如核电厂和飞机。但是个人电脑、网络服务器和智能手机(不久的将来还有生物科技和环保科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影响。硅谷恰恰在这些科技方面特别擅长。这不是一个技术有多复杂多高深的问题,而是对人类社会带来多大冲击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硅谷“钟爱”那些对社会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硅谷具有一种独特的、近乎邪门的本事去理解一项发明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颠覆性影响,然后用它大量赚钱。这就是人们称硅谷为创新工厂时的终极含义。
硅谷模式并非天生就特别适合于电脑技术的成功。不管这个模式是什么,它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高科技。硅谷代表着一个经久不衰的创新平台,它也可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它只是碰巧遇上了“信息技术”这个自电气革命以来第一个巨大的颠覆性产业。
直到2000年为止,硅谷模式可以用以下三句口号来概括:“质疑权威”、“不同凡想”、“改变世界”。硅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的出现伴随着发生自旧金山湾区而后蔓延到全世界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比如言论自由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另类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式的反主流文化,从开发西部边疆时期就已经植根于湾区的基因中。向往独立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早在硅谷的创业公司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倾向产生了发烧友们“自己动手”的信条,正是他们缔造了硅谷。发烧友们一马当先,接着是优秀的工学院,大量的政府投资,从学院到产业的技术转移,最后是大量的私人资本。如果没有那种反体制的精神,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那种反体制精神在20世纪60年代把旧金山湾区推到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当今硅谷的很多重要角色都有意或无意地属于立志改变世界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关于改变世界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湾区的高科技产业的历史,从(电视先驱)费罗·范斯沃思到(创业家)彼得·泰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年轻人的文化史,就像湾区的“其他”历史一样,从淘金热到嬉皮士,也是一部青年人的文化史。硅谷的主角常常非常年轻,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在青年时代贡献了意义重大的创意,正像摇滚音乐家和数学家一样。你无法把这种青年文化的进化和高科技产业的进步分割开来,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两个最大的科技浪潮(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和金融泡沫(网络公司热)都是年轻人创造的,同时也是为年轻人的市场(发烧友)创造的。它们代表了青年人文化的最终的因果循环。
这些特立独行的人士是硅谷故事的真正主角。硅谷不可能出现在对特立独行者不甚友善的地方。譬如说在欧洲,员工要成功就必须穿西服打领带。因此欧洲就产生了穿着考究的上流社会人士,然而他们却未必就知识渊博、能力出众和富有创造性。在湾区,即便是亿万富翁也穿牛仔裤和T恤衫,他们在发迹之前之后都一样。硅谷也不会产生在美国东海岸,正如嬉皮士与言论自由运动没有产生在美国东海岸一样:湾区充斥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极端而又另类的反建制的情绪,以及一种立志改变世界的信念。有一个比较接近复制硅谷的地方,那就是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地区,这里可以说是美国第二个最反体制的地方。
然而美国东海岸有着类似欧洲、不同于硅谷的另一方面:人员的垂直移动而不是横向移动。东海岸和欧洲都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发展,而硅谷却鼓励员工随时考虑转换工作。在欧洲,几乎没有从其他公司挖墙角的动机,因为无法合法地重新利用一个人的技能,而且利用在一家公司学到的技能去创业甚至是非法的。所以,欧洲人建立了大公司,人们主要追求的是在公司内部不断高升,而且一般都会脱离工程的领域。这种做法产生了双重效应:使工程人员在到处寻求更好听的头衔时(一般都是落在非技术的职位上)却背离了本专业,同时也限制了知识在公司内部的流动。然而,硅谷的工程师们从一家公司流动到另一家,他们在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技能,同时也实现了知识在公司之间的流动。
在欧洲,技术工作被认为比市场营销、甚至比销售工作还要低人一等。然而在硅谷,工程师的地位仅次于企业家,这也反映在工资上。在欧洲,市场和销售人员的待遇与发展前景都优于工程师。欧洲把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官员和西服革履的销售人员; 而硅谷却把工程师们变成了公司董事会的顾问或者公司创办人,他们仍然穿着牛仔裤和 T恤衫。
欧洲依赖“三大”(大政府、大工会、大公司)当然不是什么好事。硅谷鄙视的正是这“三大”。然而,硅谷的历史和计算技术的历史也表明,大政府在受到国家利益的驱动时(通常是在战争时期),会成为创新的巨大发动机。大公司如果能够高瞻远瞩也能出成果,多年来多数电脑技术的创新都出自AT&T、IBM和施乐硅谷研发中心。大型劳工团体的作用在硅谷一直缺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公司自愿担当了这个角色(惠普模式)。
“三大”在日本和英国的成功中所起的作用是富有教益的。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电脑产业必须从零开始。衰落的英国电脑产业曾在40年代领先,并拥有全部的技术诀窍,足以与美国的发展媲美。在这两个国家,政府都参与和资助了长期发展计划,并撮合了制造业界的联盟。两国最初的研究工作也都在政府资助的实验室中进行。但是结果完全相反:日本在原有的大型商社中创建了蓬勃发展的电脑产业,而英国的电脑产业却在20年内自我毁灭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湾区设法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湾区从移民中所获得的竞争优势是巨大的。人才汇聚于此是因为湾区“很酷”,它对来自东海岸、欧洲和亚洲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是一个梦想之地。湾区人口密度不高,这些移民们在这里不是代表着一个孤立的少数族裔,而几乎就是多数族群,这就鼓励着他们像一等公民一样行为处事,而不只是一个打工仔。气候和金钱当然重要,但是吸引移民们来到湾区的根本原因却是体现在职业生涯中的反体制精神。它使得工作感觉起来不像是干活,而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
正如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机遇也在起作用。假如威廉·肖克利是在田纳西而不是帕洛阿图长大,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山景城去创办他的公司,从而也就不会有仙童和英特尔,以及数十家由他的同事乃至同事的同事所创办的公司落户湾区,这些公司甚至根本就不会来到加利福尼亚。所有通常用来解释硅谷何以产生在此地的原因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所有跟“硅”有关的初创公司的老祖宗立足于此,只是因为肖克利要回到他成长的地方。
有关硅谷的一些神话有所夸大,而有一些真相又被轻描淡写。首先就拿创业辅导来说,它并不像创业导师们所声称的那样重要。成功公司的创办人拿到了资金,又创办另一个新公司,这种做法司空见惯。就获利来说这样行之有效,明星效应既能带来投资者,也会带来客户,但是却很少产生技术突破。让成功企业家重出江湖只是做市场的一个高级手法。绝大多数飞跃性的技术进步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造的,因为他们对以前的业务知之甚少。
在进化过程中一个经常被低估的因素是:行业的领军企业的缺失,对于促成创新十分重要。苹果公司完全错失了互联网的问世,谷歌完全错过了社交网的到来,Facebook很快也要完全错过“下一个大产品”。每一个这样的失误都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的巨人和一个全新的产业。如果苹果在2000年推出了一个搜索引擎,谷歌也许永远不会存在; 如果谷歌在2004年就推出了一个社交网平台,也许根本就不会有Facebook公司的产生。这些公司中的每一个都有实力轻而易举地占领新的细分市场,除非他们没有注意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硅谷公司的创始人和CEO们只对他们所创业的狭窄领域慧眼独具,但是并不擅长关注整个视野之中的震撼性变化。
湾区拥有独一无二的颠覆规则、拥抱新奇的思维理念。然而,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历史也将会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湾区成为技术从军用转民用的一个极好的典范。无线电工程和电子业最早的推动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军方在资助。
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行业的第一次浪潮是由政府项目带动的。英美两国政府资助了计算机的开发,美国航空航天局是第一批集成电路的主要用户。互联网也是政府机构的发明,然后也是由政府将之转为商用。总体来说,美国政府投资于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 而风险投资家倾向于跟进短期项目。美国政府是硅谷最大的风险投资者,也是硅谷最有影响力的战略设计者。人们也许会争辩说,风险投资者不过造成了一些投机性的泡沫而已。然而,即使是这种“泡沫性的投资行为”在硅谷也有积极作用:它加速了企业的形成和竞争。很难区分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对于硅谷的现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硅谷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难量化的因素:机会在创新中所起的作用。硅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总能让人们把机会利用到极致。硅谷人常常把工作看作是玩耍而不是任务。工作的趣味和个人的理想压倒了金钱和地位。于是就有了机会和创造性。由此看来,艺术的重要性其实是被低估了:早在成为初创公司的摇篮之前,湾区就以艺术“疯子”的避难所而著称。如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奇迹一样,硅谷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
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硅谷在一些领域成功,而在另一些领域没有成功。在激光应用方面硅谷是失败的,尽管它开始时是领先的; 硅谷也未能在工厂自动化方面有什么贡献,尽管它在机器人方面起步很早。也许是因为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有限,毕竟一个产业的形成需要一个发明家群体。国防工业为无线电工程和半导体产业创造了这样的群体; 风险投资家正在为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创造这样的群体。然而,尽管工厂自动化将会引起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但其大多数都是重工业的任务,这些重工业并不在湾区。美国国防部在其他地方创造了这样的群体,日本政府在日本也创造了这样的群体。从来没有任何人在硅谷创造过这样的群体。整合数字控制(处理器与传感器的结合)技术的方法对硅谷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
如今世界各地都在试图建设自己的硅谷,包括马来西亚的多媒体超级走廊、阿联酋迪拜的互联网城、印度班加罗尔的eCity,中国的中关村科技园等。在美国之外,与硅谷最为接近的恐怕是新加坡了,它的GDP 在2008年为1820 亿美元,还不到湾区GDP(4270 亿美元)的一半。然而,风险资本在湾区的投资在2006年达到人均1370美元的水平,新加坡则只有180美元,纽约州为107美元。另一个较为接近的地方是以色列,该国风险资本充沛,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但它却身陷中东地区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中。
在高科技领域,惟一一个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是日本,它的大规模创新改变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比如晶体管收音机(1954),石英晶体手表(1967),掌上计算器(1970),彩色复印机(1973),便携式音乐播放器(1979),激光唱片(1982),磁带录像机(1982),数字频率合成器(1983),第三代视频游戏机(1983),数码相机(1988),等离子电视(1992),DVD 播放器(1996),混合动力汽车(1997),移动互联网(1999),蓝光影碟(2003),激光电视机(2008)……但是日本的创新大都是出自百年老店的大企业:索尼、精工、雅马哈、任天堂、富士通、佳能、丰田、三菱等。很难找到一家日本公司由于一项新技术而崛起并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整个风险投资和高科技创业的现象几乎不存在。
有关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在其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的作用已经有过不少报道。但是几乎没有人论及所有这些经济增长都受益于硅谷的事实。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初创公司为东亚的经济繁荣贡献良多,东亚各国家和地区都充分对之加以利用。硅谷实际上策动着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其力度几乎可以和当地的政府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未必会发展成为当地政府所需要的样子,但是它们正是硅谷所需要的类型:高效的未来科技园区,拥有所有的工具来低成本快速地大量制造硅谷公司所需要的高端部件。地处南亚的印度也是一样,比如班加罗尔的一个软件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硅谷软件公司的需求打造的,而不是按照印度政府对软件技术的未来发展计划建设的。即便有这样的计划,其目标往往也是服务于美国的需求。中国在20 世纪90年代推行的“金字工程”建立了该国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用户,这个计划就会无的放矢,而这个用户就是硅谷。
据亚洲的媒体报道,2009年,他们的计算机产业雇用了150万人,而美国只有16.6万人。此话确实不假。不过,这150万个就业机会很多其实是硅谷创造的。
这种情况被理解成一场有趣(也有点吓人)的社会实验:硅谷在创造和投入前所未有的大量的金钱,但是却为本地创造了空前少的就业机会。投资和利润都在硅谷,但是就业机会却在亚洲。事实上,2012年湾区的失业率将近10%,是全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人们可以看到,将来高技术产业中的低级职务会逐渐从硅谷流向亚洲。诸如能源和生物科技等其他产业也是一样。
如今硅谷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20世纪那些富有创意的特立独行者已经被训练有素然而缺乏想象力的一代“书呆子”所取代,他们离了导航仪和手机,或者仅仅是缺少空调就会一筹莫展。政府对高科技的干预在减少(占产业的百分比),结果投资于长期项目的资本减少了,公众反对“大政府”的情绪使这种趋势在短时间内得以逆转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些仅仅是使硅谷今非昔比的诸多变化中的一部分,这有可能使怀旧者对未来感到悲观。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移民法、经济不景气和美元的长期疲弱极大地降低了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移民的数量。那些来到美国留学并想留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工作签证。耗时费力而令人沮丧的申请绿卡的手续,让已经拿到工作签证的人也感到泄气。湾区的创新人才中,非湾区本地人的数量令人吃惊。在湾区,移民一直是真正的创新发动机。与此同时,结构严密的硅谷社区遭到了破坏,原因是大批不具备硅谷精神的投机性移民来到此地,他们把工作机会外包到印度,把工程师们从他们的公司里扫地出门。
2000年以来的两次经济危机在业界产生了一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文化。由惠普公司所开创的众所周知的家庭式管理变成了每周工作60小时、几乎没有假期,以及任意裁员。公司和员工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仙童半导体、惠普、英特尔、施乐硅谷研发中心、苹果等公司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他们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的,他们聘用了最优秀的人才,营造了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环境。然而,到了2010年,一个工程师被聘用的机会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头公司为他们所写的个人简历如何,而不是他实际的技能和智商。实际上,任何猎头公司都会告诉你个人技能和被聘用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很低,但是一份漂亮的简历却可使你被雇用的可能性大增。这就是21世纪硅谷的实验室聘用员工的方式。
日益强大的律师的势力使这个体制产生了另一种扭曲:员工被公司裁员的机会与个人愿意付给律师的钱数成反比。一名律师更有可能代表员工从企业那里获取超过员工本人努力所能获得的某种利益。这就遇到了在欧洲跟工会打交道的同样问题,只是在湾区通过律师来捍卫一个职位,要比在欧洲通过工会与公司打交道昂贵得多。
来自学术环境的消息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硅谷的明星大学依然是初创公司的摇篮。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都已经大大扩充了学生们的活动,使学校变成一个围城。学生们没有时间旁骛校园之外的事情。这不利于同其他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人们认为,此种封闭体系是为了培养超级专家,但是却扼杀了创造性。
与此同时,硅谷和美国的基础设施总的来说有落后于亚欧先进国家的危险。亚洲人和欧洲人对硅谷的交通、技术和电子小玩意儿感到惊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一切正相反,硅谷没有任何类似于远东大都会所具有的未来风格的清洁、高速的公共交通(高速磁悬浮列车、多层单轨列车或子弹列车)。硅谷的家庭必须忍受世界上最慢又最贵的“高速”互联网服务。移动电话的覆盖普遍差劲,离开都会地区几公里就没有信号。海外的美国游客为日本和德国手机服务的强大功能而惊叹。韩国计划在2012年年底提供本国每家每户连通速度高达每秒1 G的网络,这相当于2011年硅谷最好的互联网服务给每个家庭提供的平均网速的85倍。
湾区在其他领域也深受这个国家的各种弊病之苦。麻木不仁的移民法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让已经学成毕业的留学生被扫地出门。这一切发生在加拿大、智利等国有计划地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时候。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财富鸿沟使得教育系统嫌贫爱富、比例失衡:一名斯坦福的毕业生有可能来自一个富裕家庭,而不一定就是一名世界一流的学生。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高科技地区,硅谷单调乏味、毫无特色的城市景观是一个无创意、无特点、无个性、无风格的地方的缩影。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点,那里曾经见证了非凡的工业繁荣,却没有产生过一座建筑物作为历史的丰碑。最后,湾区的高科技产业没有产生过诺贝尔奖,这一点不像另一个高科技动力之源贝尔实验室。
在另一个方面,硅谷有了重大的变化。在2000年以前,硅谷从未有过一种技术或者一个产业革命的领军企业都设立在本地的例子。英特尔在微处理器产业占统治地位,但是它的竞争对手如摩托罗拉和日本公司则不在加州。惠普是个人电脑的主要制造商,但是它的竞争对手都在加州以外(IBM、康柏、戴尔、日本和中国台湾)。苹果和网景曾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一度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它们很快被微软击败。甲骨文在数据库方面面临IBM的竞争,在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方面则有来自SAP的竞争。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硅谷的权力集中化不断强化,谷歌、苹果和甲骨文等公司竞相成为业界的霸主。谷歌正在成为网络搜索的垄断者; 苹果正在成为手持通信装置的控制者。甲骨文正在成为商用软件的巨擘。当世界走向云计算的时候,它们不仅想把自己的产品推给市场,它们更试图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人。谷歌是以互联网为中心,苹果以设备为中心,甲骨文以服务器为中心,每一家都觉得它们的商业模式与其他两家是不相容的,另外的两家必须消亡。在硅谷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不是两家,而是三家本地公司之间展开如此殊死的斗争。这使硅谷一向“友爱”的传统发生了道德上的撕裂。
21世纪的头十年也是硅谷第一次不是以“小”著称,而是要“做大”。英特尔(半导体公司的第一)、甲骨文(ERP软件的第一)、苹果(世界上身价最贵的公司)、谷歌(在网络搜索行业中遥遥领先)、Facebook和LinkedIn(社交网络行业的第一和第二名)、思科(路由器行业的第一)、惠普(个人电脑行业的第一),这些都是以前在硅谷不存在的大型跨国公司。硅谷原本是以“小”著称的。当它变成大型公司的聚集之地后,硅谷的敢于冒险的态度也可能随之改变。
但是,硅谷过去数十年生机勃勃的创新热潮留下了历久弥新的遗产,这就是甘冒风险的文化和敢为人先、接受新发明的文化。这不仅仅是个文化的问题,它的整个基础架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帮助和奖励冒险者们开发新技术。这个基础架构不仅包括了实验室和工厂,还有公司律师、市场代理、猎头公司,当然还包括风险投资者。毕竟湾区的“发明”文化一直并不那么强势,而把发明转化为成功产品却总是这里的专长,而且它越来越强大。
现在创办一个公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容易了,起点越来越低。不可避免的是,硅谷早晚会产生万维网的莫扎特,这位神童会在8岁或者10岁时,创办一个成功的技术公司。
硅谷驱动着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里,人们用智能手机接入互联网,用谷歌来搜索信息,用Facebook从事网络社交,在eBay网上购物,用贝宝来付账。不久,这个世界还将提供生物科技手段来延长人类的寿命,以及绿色科技产品来带给人无处不在的廉价能源。
硅谷不再高速发展了,它已经变成了高速发展过程的一个模板。它是一个另类的宇宙,正在吞噬着这个宇宙的其他部分。